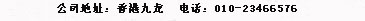视频全集破译丹布朗密码可凡倾听丹
《达芬奇密码》作家丹布朗做客《可凡倾听》。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你真的准备好了吗?五岁写就第一本书,是什么指引他前行的方向?如今功成名就,他却依然笔耕不辍。他又将给中国读者带来怎样的惊喜?本期《可凡倾听》破译丹·布朗密码,你准备好了吗?
点击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观看丹·布朗专访(上)
丹·布朗,美国当今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年出版的《达·芬奇密码》创造了一个市场奇迹,旋风般地横扫了美国各大畅销书榜,时至今日,全球累计销量超过八千万册,丹·布朗凭借这部小说从而大红大紫。除了风靡全球的《达·芬奇密码》之外,丹·布朗还创作了《数字城堡》、《骗局》、《天使与魔鬼》、《失落的秘符》、《地狱》五部小说,本本都叫座。年5月,丹·布朗首次来到中国,带来了他的最新力作《本源》,并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了一场主题为“科学改变生活”的分享会,现场火爆。与时俱进的丹·布朗这一次将当今科技文化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人工智能融入在《本源》的故事中,并试图回答那两个长久以来有关人类存在最基本的命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
曹可凡:丹·布朗你好,很高兴见到你,我很荣幸能有机会采访你。你在中国有很多粉丝,他们很喜欢你的小说,我们来谈一谈你最新的作品《本源》吧,这本书探索了人类最基本的两个问题:“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是什么引发了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丹·布朗:通常在我写小说的时候,我都有一些灵感的启发,要么是我读过的东西,要么是我见过的东西,在写《本源》的时候,我的灵感来自于我听到的东西,我听到了一段音乐,这引发了我对于生命本源的思考。我还要告诉你的是,实际上这段乐曲是我兄弟作曲的,他是一名专业的作曲家,这也是巧合,正因为此我才能提前听到了这段音乐,但是这段音乐让我开始思考达尔文、进化论、基因学,还有我们这个物种的未来。
曹可凡:从《地狱》到《本源》,你尝试把最新的社会议题与符号学联系起来,而之前的作品在这方面似乎并不明显。
丹·布朗:的确如此,我喜欢写一些宏大的理念,当然我对符号学,符号作为一种语言的概念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符号承载了许多的内涵与历史,当然,像是关于但丁的书里(《地狱》),符号学的内容肯定比较多,对于《本源》这种谈论未来的书,符号学的东西就会少一些。
曹可凡:在《本源》中,兰登问既然物理定律强大到足以创造生命,那又是谁创造了物理定律,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丹·布朗:如果我知道答案,那大家都知道答案了。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有的时候我躺在野外,注视着星空,我感到某一种力量肯定是存在的,这一切不可能是随机发生的,但有的时候我会想,不可能存在造物主,这一切都是随机事件,我们人类只是物理定律的产物而已,而定律也是碰巧存在的,并没有什么人为设计,所以我的想法时常变来变去,我现在还没有答案,我也依然在搜寻。
曹可凡:关于人工智能这个话题,你在书中提出制定严格的指导方针去管控人工智能与人类的互动。你觉得人类有没有真正做好迎接人工智能的准备?
丹·布朗:没有,我觉得我们没有准备好。但我想我们别无选择,我认为人类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我们的科技呈指数级发展,但我们的道德伦理则是呈线性发展,所以AI(人工智能)或者基因工程这样的技术给我们带来了挑战、问题和道德难题,这些难题过于先进,我们的哲学还没有赶上来,还无法解答。即便如此,我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很担心人工智能,他们担心人工智能会摧毁人类,但我们已经发明了许多可以摧毁人类的技术了,核武器就是一个例子,但我们现在依然活着,所以我认为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将始终超过我们对科技的渴求,我认为我们都会没事的。
丹·布朗出生于美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埃克塞特镇长大。父亲是一位知名的数学教授,曾获过美国总统奖,母亲则是一位音乐家。受父母的影响,丹·布朗从小就对科学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个数学与音乐相融的家庭中,他与弟弟、妹妹时常一起在父母精心设计的寻宝游戏里动足脑筋。因为只有解开密码,才是他们获得礼物的唯一途径。
曹可凡: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你的父亲是一名数学教师,母亲是一位音乐老师,父母对你的成长有着怎样的影响?
丹·布朗: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我的父母都是从事教育的,都是老师,在我成长的环境里,他们鼓励我们提问。
曹可凡:我听说你小的时候在家里常常玩寻宝游戏?
丹·布朗:我父亲很喜欢密码、谜语、解谜。圣诞节的早上我们起来,通常你会收到礼物,所有的孩子都会在早上收到圣诞节礼物,礼物都堆在圣诞树下面,你起来一看,礼物就在那儿。但在我们家,我们起来找圣诞礼物,你看不到礼物,你只会找到一个写有密码的信封,一旦你解开这个密码,上面可能写着,去冰箱那儿找找,然后你打开冰箱,那里有另一个密码,你解开那个密码,它可能会指引你上楼在浴室里面找,你跑上楼去浴室,这些线索领着你满屋子寻找,最终指向你的圣诞礼物。
曹可凡:这是谁设计的呢?
丹·布朗:我的父亲。
曹可凡:不愧是数学老师。
丹·布朗:我父亲已经82岁了,每年圣诞节,他依然为自己的孙子孙女设计寻宝游戏,这些游戏现在越来越难,当年我们的寻宝很简单,但因为现在的孩子都会上网,你可以问他们任何问题,他们都能找到答案,所以现在的谜题很难了。
曹可凡:你的父亲读了你的小说以后,他有何评论?
丹·布朗:我的父亲很喜欢我的书,他是一位十分和蔼的父亲,非常支持我,但是他也很诚实,如果我写的一些内容他不喜欢,他肯定会告诉我,但是《本源》这本书出来以后,他把我叫到一边,跟我说:“丹,我觉得这是你写最好的一本书。我非常以你为豪。”他的这番话对我很重要。
曹可凡:他有没有给你一些建议或灵感呢?
丹·布朗:有的,《本源》这本书里有些地方我就请教了我的父亲,我问了他一些书中出现的数学问题,《本源》涉及到了很多科学的内容,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是一本悬疑小说,任何人都可以读,不过里面有很多关于技术、人工智能的内容,也探讨了从科技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未来会如何。
早在孩提时代,丹·布朗就显露出过人的写作天赋。五岁时,在母亲的记录下,他创作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在完成小学九年级的课程之后,丹·布朗进入了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就读。在那里,他遇见了自己的伯乐,极其严格的英语老师杰克·希思先生。
曹可凡:我听说你在五岁的时候就写了你的第一本书,这本书讲的是什么?你是如何做到的?
丹·布朗:这很有意思,这本书叫做《长颈鹿、猪和一条着火的裤子》,这个书名太可笑了,但是在我五岁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题目。这个故事讲了三个好朋友,一只长颈鹿、一只猪和一条着火的裤子的故事,它们是好朋友,展开了一段冒险。我把这个故事逐句讲给我母亲听,她仔细地替我记录下来,然后我在旁边画画。
曹可凡:你童年的梦想是什么?
丹·布朗:很有意思的是,我童年的梦想是做一名建筑设计师,我热爱艺术,我热爱建筑,于是我开始学习画画和建筑,然后我意识到,我在这方面没有天赋,我可能在脑海里有一些图像,但是我画不出来,我是个糟糕的艺术家,但我还是很热爱艺术,所以我决定还是单纯欣赏建筑就好了,不用试着自己设计。我也演奏了很多音乐,我会弹钢琴,我也会作曲,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曲家,我也尝试了一段时间,但当时我是一名吃不饱肚子的艺术家,我的音乐没有好到可以谋生的地步,我也一直在写作,一直在讲故事,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于是我决定我想要开始写小说,这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曹可凡:你的英语老师杰克·希思相信“简洁即美”,他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丹·布朗:我不敢相信你居然知道杰克·希思,你的功课做得太棒了,杰克·希思告诉过我,当时我给他交了第一篇文章,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位英语老师,我很紧张,但是我以为我这篇文章绝对会拿到A,%,非常完美,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亚利桑那州大峡谷的故事,我刚刚去过那里,文章发了回来,我迫不及待想要看到我的A,我的满分,但结果分数却是C-,这不是一个好分数,杰克把文章里面的每个形容词都圈了出来,跟我说,不要用力过猛,他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简洁的文风能够让作品呼吸,就像你需要负空间来进行艺术创作一样,你的文章当中也需要空气,才能让作品呼吸,他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我尽可能用最简洁的方式写作,尽量让读者注意不到文字本身,你能听到这个故事,你能感觉到故事的流动,你不会被文字所分心,我不是在炫技,我是在讲故事。
曹可凡:所以当时你已经展现出了写作的天赋。
丹·布朗:我不确定我有多少天赋,但是我有很多写作的热情、耐心和学习的意愿,像所有人一样,我最开始也不太擅长,但我有耐心,也有好的老师,我非常重视,所以我练习了很多。
虽然丹·布朗的写作天赋极高,并且受过严格的写作训练,但在大学毕业之初,他并没有踏上写作道路。那时候的他,一心梦想成为一名音乐家。从阿默斯特学院毕业后,丹·布朗便跨出了校门,追逐他所钟爱的音乐梦想。不久之后,一张面向儿童的音乐专辑《动物们的合唱》就此诞生。
曹可凡:大学毕业之后,你为什么踏上了音乐之路,而不是选择写作?
丹·布朗:在大学我学习了音乐和写作,当时我只上了音乐和文学写作课程,大学毕业之后,我对自己说,我要么写书,要么写歌。出于某些原因,当时我22岁,我觉得写歌更加浪漫有趣,我想要去洛杉矶,玩音乐,认识很多女生,当然,后来音乐事业没成,认识女生也没成,于是我就开始写小说,我发现这更加适合我,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曹可凡:你是如何创作出面向儿童的音乐专辑的?
丹·布朗:是啊,这是一个古典乐专辑,里面有赋格曲,还有小小的音乐实验,曲风是古典乐,但是我用了合成声音,听上去有点像动物的声音,这是为了向我母亲致敬,她是一位古典音乐家,但是我同时对科技很感兴趣,那时合成器还是新鲜事物,我们能做出大家都没听过的声音来,所以我用合成的现代声音创作了古典乐,小孩子们很喜欢这种音乐,我还给专辑配了诗歌,这是我的第一个音乐项目,很有趣。
曹可凡:在这之后,你创作了《视角》专辑,这张专辑讲述了什么主题呢?
丹·布朗:这张专辑是我在探索我这一生究竟想做些什么,当时我处于一个非常自我的年纪,大概26岁左右,我慢慢意识到我需要成为大人了,我需要照顾好自己,我需要谨慎选择自己的朋友和职业,这些歌曲讲的就是对我们身份的探索,我们在那个阶段都会经历这样的自我放纵。
《动物们的合唱》与《视角》,两张专辑虽然自成一格,与众不同,但却销量平平。为了在音乐界出人头地,丹·布朗决心离开故土,前往洛杉矶寻求发展。但是,随之而来忙碌却无所作为的生活让他感到窒息,直至他遇见了人生中的另一半。
曹可凡:年,你离开了生活了20多年的家乡,来到洛杉矶寻求音乐事业的发展,刚到洛杉矶的时候,你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丹·布朗:说实话,我当时感到了冲击,因为我来自新英格兰的一个小镇,我从小去的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学校,我们都要穿西装打领带,一切都要很得体,我去了洛杉矶,住在好莱坞,这听上去特别,但实际上很糟糕,好莱坞是洛杉矶比较糟糕的地方,但我只住得起那里,我住的大楼里面基本上都是搞音乐的人,但这些不是古典音乐家,他们都是玩摇滚乐的人,留着长头发,带着鼻环和刺青,我就是个穿着西装领带的毛头小子,我看看周围,感觉自己格格不入…
曹可凡:你穿得太好了。
丹·布朗:没错,当时我受到了冲击,但是我学到了不能以貌取人,我遇到了很多看上去奇怪的人,但实际上他们是杰出的音乐人,也是很好的人,这是一段很棒的经历。
曹可凡:后来你加入了美国国家作曲协会,你是如何结识制作人巴里·法斯曼呢?
丹·布朗:是的,巴里·法斯曼是当年最佳的英国专辑制作人,我带着我的音乐专辑找到了美国国家作曲协会,他们说,你是一个很棒的作曲人,我说,是吗?能听到你们这么说,真是太好了,当时协会里面有很多著名的作曲人,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说,我们对你的音乐很感兴趣,我们想让你和巴里·法斯曼合作,当时巴里·法斯曼是一位著名制作人,他听了我的音乐,然后说,我们应该做一张唱片,我当时非常兴奋,因为他曾经和比利·乔、空中补给(AirSupply)等乐队合作过,这些都是我熟知而且喜欢的音乐人,他居然要跟我合作了,于是我们一起录制了一张唱片,最后大概卖了17张,里面大部分都是我妈妈买的,这张唱片非常失败,但是之后我们又做了另外一张唱片,那一张也失败了,于是我就开始写小说。
曹可凡:你是如何发行以你名字命名的首张专辑的,这张专辑背后的灵感是什么呢?
丹·布朗:这张专辑延续了我对于音乐的热爱,我热爱作曲,如果你去听这张专辑,你会发现里面的歌曲都是在讲故事,它们讲的不是我的故事,而且别人的故事,别的情景,这就是讲故事,这很有意思,因为音乐的学习和作曲的经历对我的小说写作大有裨益,在作曲的时候,你需要理解如何打造音乐张力和舒缓张力,在写作时,不仅仅要在整本小说中,更是要在每一章,甚至每一段都做到张弛有度,你需要在一个段落的开头营造紧张情绪,之后让读者放松,这样才能吸引着读者往下读,你需要理解节奏、步调和反复出现的主题,小说就像是一种音乐,一种交响乐,学习音乐帮助我理解如何设计小说的架构。
曹可凡:在制作你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你收获了爱情,遇到了你现在的太太。
丹·布朗:的确。
曹可凡:你们是否在艺术方面有很多共同语言呢?
丹·布朗:这是个有趣的故事,我认识布莱斯的时候,她是业内非常强大的一位女性,我在一个星期五下午带着我的录音带找到了她的办公室,她说:“你现在来干什么?已经下午5:05了,我要回家了。”她对我不是那么友善,再加上我当时西装革履的,她就问:“你是这个歌手的律师吗?你是谁?”我说:“不是,我就是歌手本人。”她说:“你穿着这样不可能是歌手本人。”当时她态度不是太好,但是第二天她联系了我,跟我说:“我听完了你的录音带,我很喜欢,你周一再来见我,我们开个会。”于是她向音乐行业介绍我,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在艺术方面有很多共同的兴趣,所以我们不是只聊音乐,我们也经常聊艺术。
曹可凡:在你的小说创作中,太太对你有哪些帮助?
丹·布朗:她对于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有着浓厚的兴趣,她经常会帮我做研究,我会说:“这是达·芬奇的一幅画,我需要知道里面所有的符号学意义,帮我收集所有的信息。”她会以这种方式帮助我。
END
转载请注明:http://www.jingtiao123.com/jcyzlfy/90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