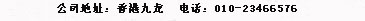男友消失3个月,我找到他住处却被告知他和
本篇文章收录于百家号精品栏目#百家故事#中,本主题将聚集全平台的优质故事内容,读百家故事,品百味人生。
1
一年中的最后一天,曲枝抵达哈尔滨机场。飞机落地正好是晚上十一点,地面温度接近零下三十摄氏度。
刚出机舱,风就钻进四肢百骸里,冻得曲枝直打哆嗦。她把帽子围巾紧了又紧,好不容易等来了机场摆渡车,她这才把下意识蜷起来的身子放松开。
又等了一会儿,酒店接客的车才姗姗来迟。
夜色沉重,曲枝隔着结了厚厚一层冰花的车窗往外看,隐隐绰绰中,路两旁的行道木支棱着光秃秃的枝干,像蛰伏在夜色中的细长人影。
曲枝突然就想起了宋嘉木。
曲枝和宋嘉木的相识很戏剧化。五年前,远在重庆的曲枝收到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信封是黄棕色的牛皮纸,里面再套着一个白色的小信封。
她打开那个小信封,抖出里面仔细折叠的一张白纸,上面就写了一句话——
“希望我能长命百岁。”
一年前,高二文理分科前曲枝和家人一起去北京旅游,大大小小的景点都转遍了,最后她在艺术区一间古朴雅致的小屋子里给未来的自己写了一封信。
本来她填的寄信的时间,应该是在在一个月后。
而隔了一年后,曲枝捏着这封寄错了的信啼笑皆非。她该写封信回去把那家店骂一顿,还是按照白色小信封上留下的地址致信这位想要长命百岁的朋友,告知他信被错寄了?
曲枝埋头刷五三,摇着笔杆子想了好几天,最终决定把这封不该被她看到的信寄到它本来应去的地方。
做这个决定时她正在复习,手边摆着一本草稿本。她伸手拿过,想也不想地撕下一角,缺口参差不齐还带着毛边,写——
“这位想要长命百岁的朋友,不知你是否去过北京的艺术区?是否在里面一家店留下一封信?如果符合以上两点,首先我很抱歉地告诉你,你的信被错寄到了我这里。其次,店家寄信的时间实在不凑巧,正好赶上了愚人节,我以为是谁在开玩笑,所以看了你的信。万分抱歉。”
想了想,又在最末添了一句:“冒昧地问一下,您今年贵庚?”
第二日,晨光熹微,路过邮局的曲枝花了三分钟的时间,记下了那个地址并将封信连同自己破烂的草稿纸一起寄出去了。
半个月后,小区前的石榴树上开了第一朵花时,曲枝收到了回信。
信是从一个新的地址寄过来的,信里有她随手撕的那张稿纸,并一张叠得方正的纸片。
稿纸被人沿着缺口勾勒,以细腻的笔触,变成了一朵榴花样的画。而那张方正的纸上只写了两句话——
“没关系。另:我永远十八。”字迹刚劲张扬,透着一股勃勃朝气。
那时的曲枝捧着这两张纸,嘴角咧到了耳根去。
2
曲枝抵达哈尔滨的第二天,她从机场转乘大巴去了市区。
市区街道上的车辆拥堵在一块儿,喷出白色的尾气袅绕腾起成了云,俄式建筑风格让这座城市添了几分异域风情,白鸽绕着屋顶拱起的塔尖转了一圈后又飞快躲回了巢中。
曲枝朝着手心呵了一口热气,走进路边的一个咖啡馆里。
纵使外面冰天雪地,哈尔滨的室内也一向是温暖如春的。咖啡馆小妹瞧着有些犯困,怏怏地撑着吧台煮咖啡。
曲枝搓了搓冻僵的手,趁着这个间隙,从包里掏出一张纸来写信。
“亲爱的宋嘉木,你一定猜不到,我是在哪里写下了这封信……”
落地玻璃窗外是形色匆忙的路人。曲枝停笔时,热气腾腾的咖啡正好被端上来,她捏着小勺搅了搅,精致的拉花扭曲盘旋,变成一只安眠的白鸽。
曲枝的心理素质不好,高考前半个月开始焦躁。她整宿地做噩梦,梦里是张着血盆大口的兽,咆哮着将她追赶至万丈悬崖,然后她惊醒,便再也睡不着,只能睁着眼熬到天明。
而在这些无眠的深夜里,抛开元素向量、单词电场外,她想得最多的,就是宋嘉木了。
她第二次给他写信时,规规矩矩地买了描花边的信纸。信纸带着些浅淡的纸香味儿,后来她摘了石榴花放进去后,信纸边沿又沾染了浅淡的红。
“这位永远十八岁的陌生人,你好。我想你应该看一下,石榴花长这样。”
不久之后,宋嘉木回她:“我叫宋嘉木,另,不是我不会画石榴花,实在是你撕纸的手法太刁钻,我尚且无力驾驭那些带着毛边的线条。”
这么一来一往,联系竟这样保持了下来。
八十分的邮票可以走遍全国,窄小的羊皮纸信封里,装着的往往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有某天清晨落在窗前的一根翎羽,有丛生攀爬在栅栏上盛开的一朵蔷薇,还有复习至某页,看到那个日渐熟悉的地名时忍不住将整段话抄写下来的字条。
宋嘉木的回信相对来说则要简单一些,大多都是画。不同颜色不同景象,线条色彩堆砌在一起,描绘出张扬放肆的、说也说不尽的少年意气。
其中有一幅是曲枝最喜欢的。他在收到了她说她睡不好的信后画了“食梦貘”送过来。
传闻食梦貘会吞吃噩梦,让人安枕。那时曲枝抱着这幅画,嗅着窗外吹来的浓郁草木香,果真香甜地睡上了一觉。
曲枝端起咖啡轻啜一口,醇郁的味道在舌尖弥漫开,泛为一丝苦涩。
只是后来她在各方面的考量之下报了一所北京的医科大学,到底没去她逐日开始挂念的那所冰雪之城。
天边有阴云堆积,落雪纷扬洒落,远处屋顶已积了一层雪白,这是第一场雪。曲枝想起她刚上大一那年,宋嘉木第一次给她寄了除画以外的东西。那是一个拇指大小的瓶子,里面盛有半瓶晶莹剔透的水。
他附信写道:“送给你,哈尔滨的第一场雪。”
那时曲枝明明心里甜得要死,还是故意回他:“你不会是随便装了瓶水来糊弄我吧?”
宋嘉木愤然回道:“不信你自己来看啊,北京离哈尔滨这么近!”
可近的定义是什么呢?北京其实离哈尔滨有一千两百公里。
曲枝将脑袋抵在咖啡馆冰凉的玻璃上,轻轻眨了眨眼。
只是等她终于离他这样近了,她却找不到他了。
“宋嘉木,你已经消失了……整整三个月。”
3
临近午时,天放了晴,太阳拨开厚重的云层,光洒在路旁的雪堆上,让人瞧着也觉得暖和了些。
曲枝按着地址寻去了一曼街的一个胡同里,这里的位置靠近哈医大一院。
一曼街位于道外区。市中心街景繁华,吵嚷不堪。曲枝拐进了小区深处后,身后人群嘈杂的声音这才小了一些。
这胡同的环境并不好,坐落在一个狭仄的小巷里,一条只够让两人并肩行走的灰砖路上满是结成了冰的脏水和在太阳底下锃亮的油污。
曲枝小心地避开那些被涂抹得乱七八糟的黑墙。
宋嘉木住在第七幢搂。楼底下垃圾桶里的垃圾堆得冒了尖,被冻在一块儿,看起来突兀又怪异,像是女巫头顶的帽子。
曲枝盯着瞧了一会儿,想象着宋嘉木哆哆嗦嗦从五楼跑下来扔垃圾而后又迅速跑回去的场景。
宋嘉木是四个月前搬来这里的。那时正值夏末,天气开始转凉,宋嘉木的感冒又变得严重起来。
开春的时候他去了松花江写生,结果回来就生病了,他在信里简单地和曲枝提了几句,字里行间都透着漫不经心。那时医院实习,每天生生死死见多了,便也没把他这点病放心上,不想过了三个月,宋嘉木在信里偶然提及,他的病竟还没好。
曲枝这才重视起来。可她见不着他,不知道具体病症,最后也只能提笔殷殷嘱咐,啰啰嗦嗦写满了三大页纸。
又过了半个月,曲枝收到回信时,宋嘉木信封上填写的地址已经换成一曼街了。
那是宋嘉木给曲枝寄的倒数第二封信。
信中他说起那凶横傲慢的新房东,总是在大清早就带着她家的德牧叮铃哐啷下楼去撒尿,有脾气不好的住户隔着门板骂她,那房东就牵着狗在门外和人吵起来。靠着两句“你再吼一句试试”“吼你咋地”来回争个不休。
那时北京夏暑未褪,曲枝下了课回寝室躺在床上看信,天花板上的小风扇嗡嗡转着,她捂着肚子笑个不停。
待看到信末,她笑得更欢实。
他这样写道:“我觉得你的毕业旅行,可以来哈尔滨。”
楼并不高,七八层的样子,所以没有安电梯,曲枝借着楼道间昏暗的灯光逐阶往上走。声控灯照明的时间极短,她每上两步楼梯就得跺一跺脚。
有人推门探出一张圆鼓鼓的脸,皱眉呵斥:“大中午的,不知道小声点啊!”
曲枝瑟缩了下,瞧着五大三粗的女人,讪讪指了指对门:“请问,5-2的宋嘉木现在还在住这儿吗?”
女人打量了她几眼,神情放和缓了些:“早搬走了。怎么,要租房?”
曲枝摇了摇头,小声道:“不是,我来找人。”
那女人便又不耐烦了,拉下脸来:“走了,三个月前跟一个女的一起搬走了。”
曲枝有些愣,瞧着眼前被甩上的铁门,半晌没回过神来。
过了一会儿,门又被打开,女人拎着一个亚麻色帆布包出来,粗鲁地往曲枝怀里一塞:“也不收拾干净些,你既然认识他就拿走吧,别说我昧了他的东西。”
怀中的东西有尖尖的棱角,刚好抵在她的心口,传来一阵尖锐的疼。曲枝隔着粗粝的布摩挲着,描摹出它的形状来。
是一个画夹。打开来看,里面夹着一副未完成的画——
梵高的《向日葵》。
他只上了一半的色,绚烂璀璨如阳光的金黄,只是画的边沿却不知为什么,留下一抹暗红色的凝固了的水彩。
看着突兀极了。
曲枝带着东西缓缓下楼,末了,站在楼前,举起手将这幅画空白的另一边对向天上的太阳。
她瞧着那力透纸背的光,不停地挪着位置,让它与上了色的那一半合为一体。
梵高的向日葵,太阳本身,象征生命的永存。
4
第三天一早,曲枝去了古香街的胡同里。这是宋嘉木第一次给她回信时填的地址。
事实上,后来两人的联系,也多是在这里。
宋嘉木总是提起胡同口的豆浆店,他每天早上都会买一袋香醇的豆浆,再去包子铺买两个包子,然后拨开围巾,咬一口包子喝一口豆浆,慢悠悠地穿过街道,背着厚重的画板去学画。
他在信上说他到的时间总是很早,他的师娘刚起来做早饭,电饭锅里煲着粥,咕噜噜冒着白泡泡,平底锅里煎着蛋,金黄的油滋滋作响。师娘带着围裙,看到他的时候会弯起眼笑,说:“嘉木来了呀,快坐,早饭马上就好。”于是即便他吃了早饭,也会假装自己没有吃。
他在信上说,他的师父家里有一个小女孩儿,师父师娘宠着惯着,视她为掌上明珠,唤她娇娇。可娇娇不喜欢师娘做的早饭,每天早上都要跑出去吃。
他在信的末尾说:“我不喜欢娇娇。”
宋嘉木曾经告诉过她,很久以前,他的父亲便患病死了,后来,他的母亲也死在了一场大火里。若不然,他也该是这样娇宠长大的孩子。
胡同里种了一排垂枝榆,冬天掉光了叶子,剩下光秃秃的枝条挂满了冰晶。他说每到冬天他路过这些树都会担心上面的冰凌子落下来砸到他的脑袋。
于是等如今曲枝来时,也下意识地绕开它了。
直到她走到某一棵树下。
那棵树旁有栋三层小楼,只是一楼的铁门关得严严实实,曲枝趴在上面摁了好一会儿门铃,才听到楼里传来拄着拐棍下楼的声音。
“谁啊?”有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曲枝搓了搓冻僵的手,回道:“您好,我是来找人的,请问宋嘉木还住在这里吗?”
宋嘉木说过,他的房东不常在国内,于是一栋楼任由他作威作福。春天他坐在窗前画垂枝榆,为给自己的画架腾位置,把靠窗的小沙发搬得哐哐作响,等夏天房东回哈尔滨访友,看到被放置在角落快蒙上一层灰的沙发,气得找他理论了好久。
“不过他是个极好的人。”宋嘉木后来又回信跟她解释,说房东常年住在英国,行事做派很是绅士,在得知宋嘉木搬沙发是为了画画后,不但没有再生气,反倒是很慷慨地送了他一套画具。房东也偶尔会从英国给他寄一些礼物,有英国红茶,有酒心巧克力,甚至有一次还从乐队博物馆给宋嘉木寄了一张黑胶唱片。
那阵子宋嘉木开心极了,连着两个月给曲枝写信,三两句就得提一下那张唱片。
曲枝也跟着开心,从手机的音乐软件上买了那张黑胶唱片的专辑,晚上听着他们的歌睡觉。
仿佛这样,她和宋嘉木就能再贴近一些……
铁门吱呀一声被打开,一位衣着得体的老人走出来,温柔地对她笑了笑:“不好意思小姐,你找的人四个月前就搬走了。”
“这样啊……”风吹得她的眼睛有些涩,她垂眼,轻轻点了点头,道过谢后转身欲走。
老人却叫住了她:“天太冷了,可否容许我为小姐倒杯热水?”
当真是英国老绅士的做派,在征得了曲枝点头后,才回屋去倒来一杯热水。
“小姐,祝你好运。”房东最后说道。
“谢谢。”曲枝端着热水站在垂枝榆下,指尖划过纸杯的杯沿,好一会儿,才在热水腾起的袅袅白气中抬头,轻声询问道:“不知道您方不方便,将宋嘉木的联系方式给我?”
胡同口的豆浆铺子没开门,曲枝从胡同出来时驻足看了一会儿后,沿着街道慢慢地往前走。
她住的那所旅馆就在街道的尽头,等走了一会儿,她掏出手机来,摁下了今天新存的那个号码。
两声提示音后,电话被接通,一道沙哑低沉的男声响起:“你好。”
曲枝顿了顿,声音在风里变得细微:“宋嘉木,我是曲枝。”
电话那头的声音滞了两秒,然后,迅速掐断了电话。
街道还没有走到尽头。
曲枝拐进路旁的一个饮品店,抬起被冻得通红的眼,问:“这里有热豆浆卖吗?”
5
也许女性的精神天生便具有韧性,即便意识到什么,可不到最后一刻便不肯死心。来哈尔滨的第四天,曲枝去了一个地方。
当年被错寄到她手里的那个白色小信封,写着的地址就是这里。
这是一片傍山而建的别墅区,各种户型的小洋楼错落排布在树影里,被雪覆盖,并不十分好辨认。
有老大爷在鹅卵石铺就的小道上晨练,甩着膀子来来回回走。
曲枝在里面徒劳地绕了一圈后,捏着写了地址的纸条去求助:“大爷,请问这个地方该怎么走?”
“这不是南边的宋家吗?”老大爷接过纸条一看,花白的眉皱起来:“小丫头去那儿干啥,那里早就没人住了。”
曲枝抿了抿有些干燥的唇,小声道:“不干什么,就是去看看。”
“你这丫头,那儿有啥好看的?五年前就被烧光了,只剩下黑漆漆的一个墙架子。”
老大爷转着手里沉甸甸的钢珠,语带惋惜道:“当年火起得很快,消防兵还没来呢就烧红了半边天,我们住在这里的人一边打水救火一边寻思着,里头的人估计都活不成,谁曾想,有个孩子硬是自己从火场里爬了出来。”
“那……后来呢?”像是喉间灌进了风,曲枝的嗓音有些哑。
老大爷摇头叹息:“不知道去哪儿了,听门卫说四年前的春天那孩子回来过一次,再后来,就没有人见过他了。这孩子呀,当年也是个讨喜的,生得好嘴又甜,哄得这片区的住户都喜欢他……”
说完,他伸手往南指了指,“你要是非要去,就循着人声走,我听人说今儿一大早就有好些人往那儿去了,据说是开发商去评估那块地皮。”
曲枝便依言向南走,果然,等她抵达的时候,已经有好些人围着那漆黑空洞如同怪物的房子在测量了。
枯枝裹在白雪里,曲枝未察觉,一脚踩上去,发出咯嘣一声响,有人发现了她。
“来干嘛的?”那人有些不耐烦,“没事就赶紧走,我们在工作呢!”
桧柏间积着零星的雪,擦过曲枝的手臂后,枝叶轻摇,雪便像白羽般扑簌簌抖落一地。
曲枝走到那只漆黑而又庞大的怪物下,仿佛又回到了高考前的被兽追赶至深渊的那个梦里。
她听见自己有些艰难地开口,“请问,是谁委托你们来的?”
“还能有谁。”那人可能是见曲枝的脸色有些不对劲,这才耐着性子回道,“自然是这家的主人。”
“他叫宋嘉木是吗?”
“你认识?”
曲枝对这话恍若未闻:“那他有没有说,为什么要把这块地给卖了?”
“这谁能知道。”想了想,那人猜道,“没准是卖了房子拿钱哄身边跟着的那个小女朋友的欢心?”
身边的人便都心照不宣地笑起来,剩曲枝点了点头,目光没有落至任何一处,像是在自言自语般:“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绕了一圈,才发现这到底不过是他的一个弥天大谎。曲枝突然蹲在地上,难道自己居然被骗了五年?这到底怎么回事?(小说名:《春逝》,作者:钟无羡。)
转载请注明:http://www.jingtiao123.com/jcyjwzl/8907.html